以下内容从当代学术棱镜翻译系列的“文化研究指南”中选择,第11章,“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共生趋势”
本章由John Nguye Ernie撰写,由Pan Chunlin和Wang Xiaolu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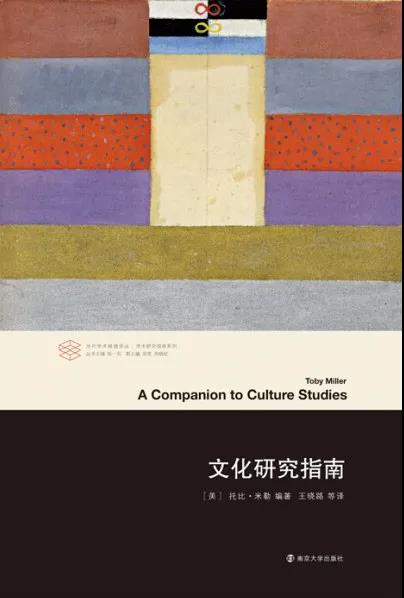
意识形态批评在媒体研究中的首要地位
我已经在上面强调了:从历史角度来看,对于文化研究,重组媒体研究的关键在于葛兰西对历史条件和社会权力机制做出反应的方法。重要的是要注意: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不用于文化和交流理论,而是为建立更广泛的媒体效应的历史性联系提供了必要的脚手架。为此,1970年代的文化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项基于经验的媒体研究,其中提供了意识形态批评至关重要的例子。这是对Hall等人进行一般性重新检查的教育。维持危机。
1972年,抢劫被列为谋杀案,抢劫在英格兰的汉兹沃思进行了审判。这种罪行引发了媒体,司法系统和公众的巨大反应。尽管至少从1860年代起,这种犯罪就已经在伦敦街头司空见惯,但媒体和警察将其描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分类犯罪”。在短时间内,关于这种“新型”犯罪的公众辩论无止境,它引起了人们对“英国生活方式”的道德结构以及英国法律和瓦解的明显削弱甚至崩溃的恐慌。命令。到1976年,辩论似乎集中在一个实际的“来源”:贫民窟市中心的黑人青年。那时,抢劫和黑人成为公众想象中的代名词。
围绕Handsworth案的恐惧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威胁。在这种恐惧的推动下,社会控制变得越来越严格和“正当”。从怀疑的角度来看,监视危机的作者指出,对Handsworth案的分析发现了整个抗议部队的分析,从幕后和幕后形成了与霸权斗争有关某些政府设定控制权的是犯罪本身,而是关于被认为与犯罪明显相关的社会群体:黑人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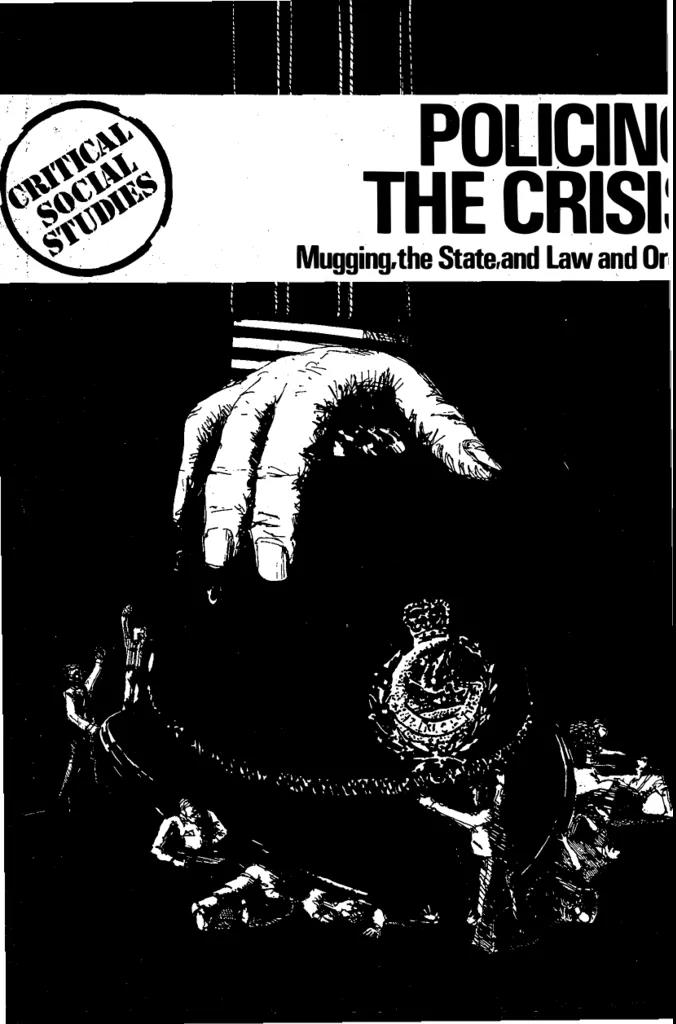
“监视危机”
“监视危机”将意识形态批评从互动模式转移到结构和历史模式。 “累积抢劫”不是被认为是公共传播圈中消费的事实,而是社会力量和冲突之间的“累积”……存在着更广泛的历史环境。他们认为,确切地说,这一历史事件是“以特殊方式煽动抢劫的关键力量”。因此,Handsworth案展示了媒体操作的结果。从此,通过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新闻过程的形成及其与霸权的关系。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理论,即表达理论,为通过对犯罪和黑人青年的(高度紧张)控制及其明显的团结而维持社会稳定的新闻和法律机构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监视危机揭示了对话,对黑人的态度和实践的压制领域,所有这些都在解释了Handsworth案件和随后的事件结构之前解释了如何“适当”的“适当”响应,控制和监测。
“监视危机”中使用的方法和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个重要的转弯详细研究了其伪装关系中的中性事件,作为复杂的信息网络,在公众的想象中获得声望(“常识”),并坚持改变社会监视和现实的可能性。例如,这个可怕的,现实的,现实,现实的谋杀故事在1988年,“准备生活谋杀案”成为一项重要的媒体活动,是由查尔斯·阿克兰(Charles Aklan)在他的青年时期kaiyun.ccm,谋杀案中创建的意识形态内容与种族化的青年和监视工作有关。厄尼(Ernie)在不稳定的边境中围绕艾滋病药物(AZT)的“发明”开了媒体对话,并解释了其意识形态意义在某些媒体权威和偏差事件中的意义。恢复管理。这些例子证明了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在理解新闻中的影响。显然,与许多竞争对手在文化研究中的看法相反,这些例子中发现的意识形态批评不仅限于文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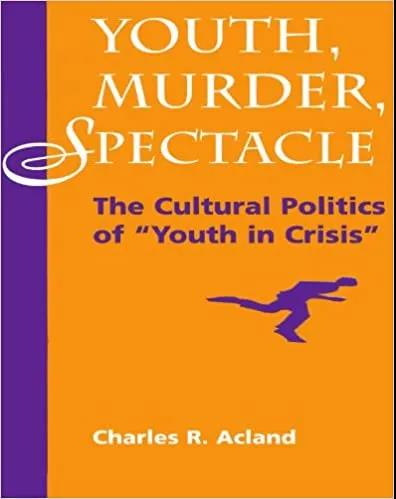
青年,谋杀,公开展示
同时,出于某种未知原因,意识形态途径被霍尔的“偏见解释”概念过于重视,这绝不限于文本解释。在过去的几年中,正如媒体研究转向意识形态模式一样,我们也从“偏见的解释”研究转移到霍尔媒体效应模型的其他(自发)元素,即文本和上下文的负面解释和对抗性解释。因此,在媒体研究和对这些研究的理论修订中的受众接受研究的持续发展试图概念化和追踪媒体消费环境中发现的相关受众。
与围绕流行文化研究的合法性政治不同,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实施的媒体受众研究使自己分享了人们对人种学传统的知识统治的批评。其中一些异议未能将媒体的消费环境视为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开yun体育app官网网页登录入口,该形式具有自己的解释社区组织,互文开放性,谣言和其他日常生活实践的中心主义。重新考虑媒体研究现场调查的“领域”的努力导致了重新思考民族志及其方法的努力。在一个媒体消费在超信息环境中的时代云开·全站体育app登录,就像文化研究面临着发明新的媒体用户研究模型(可能是人类学,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一样,它似乎要求更多。 “安全纪律基金会”及其“既定方法论程序”的回归将产生不利的后果。
媒体研究的界限: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媒体批评来自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其区分来自政治斗争中的共同点。同时,两种调查的分裂有时是错误的。但是,一方面,对媒体的工业实践和结构的复杂分析通常包括:解释性过程和对资本的全面理解(这里的“资本”表示“福特主义”或“后福利”,“资本” “资本主义”或“后福利主义”)如何重建媒体实践中的社会,经济和话语关系。另一方面,媒体研究是一种“文化对话”,包括流通和消费期,通常始于对周围物质条件(如果不是“建筑”)的充分调查,这种对话与其意识形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状况。显然,沟通和媒体是复杂的系统,包括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
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但是它们不能简化为以下“双重区别”,例如具体和抽象,朴素和深刻,研究与理论,客观和主观等。
在媒体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内部整合似乎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调整(尤其是“经济决定论”。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的重新解释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结构“将上层结构”确定为不同尝试,这种调整是在媒体文化中充满“阶级关注”的框架和时代。调整的中心是考虑整个媒体消费方式。
首先,文化研究假设文化消费被视为以商品化过程为主的文化产业,这导致了政治计划的破产,尤其是对于左翼政治计划。文化研究倡导者:社会不能溶解在经济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无保证”流行文化政治的批判性研究转向了意识形态的方向。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途径的主要盲点上。当人们消费“媒体”时,资本主义媒体就会融入社会生活,而不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制造”。文化研究表明,除非认真对待这一理论化过程,否则沟通和媒体研究将陷入对政治确定性的误解,并且似乎商品逻辑将完全限制我们与媒体关系的各个方面。
其次,文化研究认为,媒体研究需要对媒体研究人员和媒体消费者进行更开放的看法。即使在1985年Laclau和Murphy称其为“社会过度供过于求”的时代,政治经济学也未能理论化这些社会差异。例如,对电影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扩大劳动力剥削和日常实践的经济结构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行业对妇女和文化少数群体的不同影响。即使在格拉斯·戈梅利(Glas Gomery)对美国电影历史的复杂研究中,黑人电影院和其他种族也被视为“选择性行动”,而在这个假设上,将工业企业的电影运营实践和贸易置于了这一假设上:集中资本和分散的电影观众之间的直接关系。换句话说,资本的运动和利润无疑解释了媒体消费中分离的社会现实。从广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媒体职业现象。文化研究主张,历史上的“社会”由远远超过“经济”的力量组成。即使是劳动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调查的主要调查点,也是社会问题。即使在劳动剥削持续整合的背景下,撤销法规后的媒体行业也需要促进一场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对话,该对话暴露了“自动化”,“本地控制”,泰勒主义的“效率”,“效率”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减少全球支出。

近年来,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已经加深。我将在这里进一步研究这场战斗。我同意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高级学者文森特·莫斯科的观点。他总结了这两个方面之间非常流利和隐性话语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长时间的报价:
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其工作(沟通分析)主题植根于试图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普通人的需求,目标,冲突,失败和成功;即使他们面对一个并非完全由自己和象征世界建立的系统。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其控制之外表现出敌对的力量。文化研究还有助于扩大关键作品,这超越了阶级分析:女权主义和受新社会运动的启发。例如,和平与环保主义。这些作品提醒政治经济学,尽管社会阶层是一种核心分界线,或者从所采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与多样性构建的起点重叠的层次结构。此外,尽管其极其公式化的表达庆祝当代生活的政治是对建立政治抵抗的特定身份的追求,但文化研究已经以许多方式认识到社会机构提供的潜在能量,这在政治和经济分析中很少关注。






